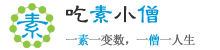我并不是个十分讲情义的人,小的时候舅舅成天骂我,说我是天生的白眼狼,还说黄眼珠子六亲不认,很想要问他我的眼睛究竟是白啊还是黄呀。每次我姥姥打回来桃酥饼干,本来就不多,他还一次吃好几块。后来我总会偷偷藏起来一部分,然后提前告诉他吃完了,反正在舅舅的心里我也就这样了,永远摆脱不掉没有良心这条印象。大概也是因为有这么个舅舅,我从小心理暗示便开始破罐子破摔,反驳别人的时候总是说,我又不是什么好人。可这他妈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?
看着周围有人在哭,我有种说不出来的别扭,自己居然真的一点儿眼泪也没有。我想不通自个儿为什么要站在这儿,难道只是因为不小心翻开刘宁的微信朋友圈吗,那个已经交给她妈妈使用的账号,整天转发一些中老年妇女关注的养生知识,还配上一些分辨率很低的图片。人的有些想法真的很奇怪,比如下一秒你就可能爱上恨的那个人,又比如死了那么久都没怎么关心过的人,今天却突然决定要给她扫墓。
天是很蓝的,太阳很好,和记忆中的一天很像。不过那又怎样呢,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。
再次见到徐烨,是发生在十分钟前的事情。我感到有些惊讶,但一点也不意外。我俩到底有多久没有见过面了,这个不重要,总之好久好久了。我不清楚他是不是每年清明节都会来看她,那她真的是个不幸中的幸运人,死后依然能被一个男人在固定的时间想起。
现在有了公墓挺好的,过去很多普通人家都是野坟,甚至连块像样的墓碑也没有。经常是孩子们把带过来的食物都快要吃光了,有大人才突然想起来上错了坟。记得我第一次上坟扫墓,大概七八岁的样子,是为了我祖爷爷。我没见过祖爷爷,也不懂得悲伤,只觉得兴奋。趁大人不注意我爬上了一座低矮的小山丘,结果被我妈一脸诧异地给拽下来,后来才知道那座山丘下面埋的就是我祖爷爷。那时我感到伤感,很不理解,人怎么能永远待在一座局促的山丘下面呢。
每次站在老家门口那条暗黑的河流前,都会忍不住想象已经不存在了的人们。有些时候真的很害怕自己也会顺着那肮脏的河水流走,和提前熟透落入水里的枣一起。
刘宁的墓旁开着一种淡黄色的小野花,还不难看。墓碑上的照片是研一那年我们一起去北京,我在雍和宫给她照的,她坐在绿色的木头长椅上面,背后是一大堵砖红色的墙。那张相拍了好几次她才算勉强满意,我实事求是,但她硬是说我把她的腿给照短了。照片里的刘宁看不出来悲喜,玩世不恭又很认真的样子,就像她早有预感一样。如果知道那会是她人生里的最后一张照片,兴许我就好好拍了。
她家里的人大概都回去了,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一束鲜花。相比别人的坟墓,她生前的人缘真的不怎么样,没有什么朋友,好不容易交到一个,还是我这种薄情寡义的人。不过更大的可能是我们从来也不算朋友,毕竟刘宁看不上大多数人,其中应该也包括我。
离开墓园时,我问他打算怎么回去,他说等公交。那趟公交车每次都要等上很久才能等到,这里的天似乎总是黑得很快,待会儿太阳一落山活人就没有几个了。我说:那我捎你一程吧。
他想了一下,说:行吧。
怎么不开车过来?我随口问了一句。
让我老婆上班开走了。他说。
我有些微小的惊讶,或许是失落,我说:你都结婚了。
你呢?
也快了吧。我说
汽车在沉默中行驶了一段路程之后,我想要询问他的目的地,他却先开口:你饿不饿,一起吃个饭吧。
我看了下时间,可能他没有注意到吧,现在就不是个吃饭的点儿,但我还是说了声好。
我们仿佛两个刚刚获得救赎的人,逃离沉默后开始天南海北地聊吃,侃哪家饭馆的服务到位,哪里的盐总是放得太多。内后视镜里的徐烨显得有些焦灼,似乎有事情难住了他。进入市区等候红绿灯时,我说:你要上厕所吗,前面有家肯德基。说完我感觉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那是一座公共厕所一样,但平时我们也是这么问别人的。
他愣怔了一下,说:不用了。
我们在新天地门口停车,他说四层有家料理挺好,我说那就这儿吧。刚下车,徐烨迫不及待地掏出一根烟给了我,又给自己点上一根。
我说:想抽烟怎么不早说?
他说:算了,车里面不抽。
我笑:你还是那么表里不一啊。
这时我才注意到他的某些局部的细节,穿戴每一处依然一丝不苟,只是面相早就不似从前,看起来像个精神而疲惫的中年人了。二十九岁应该就算是中年了吧,但我从不认为自己中年,因为我几乎不照镜子。有时一觉醒来,还以为该上学了。也许只有等到我五十岁的时候才会觉得二十九岁很年轻,基本上还是个孩子。
我说我不太饿,他说他也不太饿,抽了好几根烟之后我们才开始点餐。看见菜单上的盐焗蜗牛想起刘宁来,有段时间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饭馆,她死活要让我去尝尝他们家的蜗牛。她说这是那里的特色菜,蜗牛的个头巨大,而且味儿入得还好。我说我有点不太忍心,她说没关系,你吃完就忍心了。我一直都很怀疑那馆子是不是她家开的,要么就是和蜗牛有世仇,不然提蜗牛她亢奋什么。
我说:来份盐焗蜗牛吧。
他的眼神里似乎捕捉到了什么,迟疑了一秒钟,把我的话给服务生重复了一遍:一份盐焗蜗牛。
过了很久他说:她貌似也爱吃这个。
我没说话,假装没有听到,或者干脆觉得没有发出声音的必要。我在想,我和徐烨到底算不算朋友呢,其实我很不喜欢使用这个名词,也许连名词也算不上,顶多是个虚词。所以我们应该不算朋友,就是个老同学。
你每年都去看她吗?我试探性地问他。
没有,今年是头一回,他说,差点没有找到。
我似乎有些高兴,天知道我有什么可高兴的,他去不去和我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。
我说:你老婆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?
他说:我没有告诉她,她不知道我要来。
我说:哦。
他看着菜单,说:你要不要吃焦糖布丁,女生一般都爱吃这种玩意儿。
他居然说女生,我都二十九了,女生叫得我有些脸红。我也没有细想焦糖布丁入嘴后的口感,没有想那种感觉是不是会使自己感到愉悦,如果愉悦说明爱吃。但我顾不上这么多了,我的脸很红。我说:哦。
他说: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?
他似乎很热衷这个话题,很有意思吗,一个女人结婚了还有什么劲。如果我是男人,我就不和对方聊结婚。结没结是一码事,谈不谈是另一码事,仿佛只要不谈大家就都是单身一样,而只有单身才有无限的可能。
这条微信来得很是时候,我假装很繁琐的样子在鼓捣手机。尽管已经很努力在克制自己的情绪了,但他还是察觉到了端倪,说: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?
嗯,我说,也不算吧。
男朋友吗?
男朋友。我说。
他没有问我是不是需要立刻离开,他好像不太想问,我更懒得说,然后也就不了了之了,反正的确不算什么要紧的。况且,外面开始下雨了,总得让人家把饭吃完。
读研究生那会儿还不太流行使用微信,估计我们算是最早的一批使用者了。玩的人少,能添加的好友不多,刘宁自认为隐私空间还比较大,在上面发一些照片,一些一时兴起的语言。她不知道,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在玩,但从来不发东西,也不和她说话。
刘宁算得上是美人了,但脸蛋儿漂亮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,还不至于蔑视天下。她没有什么同性的朋友,异性的追求者却永远充沛不竭。每逢节日,她总能有一大堆的礼物可以收,对于学生而言那些礼物都算得上价值不菲。她不爱人家,也不拒绝,就这么钓着各种男人的胃口,还一副根本没有觉察的样子。更厉害的是,刘宁的那些追求者彼此之间都可以和平共处,彬彬有礼,关系甚笃。而她依然可以保持单身的清高,在其中不费力地周旋。最可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,她确确实实不是在故意算计什么,而是真的善良无害。
本来我都可以忘记那个天真的婊子了,但没忍住进了她的朋友圈,翻到以前的东西。那些照片里有一瓶是当时最新款的香奈儿香水,徐烨送她的,而那天我也在。于是,我再一次想起了她。我想我要是个男的就好了,就上了她,上了她也许就不那么气了。再或者,她就干脆躲我远一些,不要对我太温柔,这样我可以肆无忌惮地恨她。
不明白刘宁为什么爱吃这种东西,还不如在家门口的小饭店吃一盘鱼香肉丝盖饭。徐烨点多了,我们没吃完。他看起来没有要回去的意思,我无所谓,跟着他在商场里漫无目的地绕。
你要玩儿吗?他站在游戏城门口说。
那种东西有什么好玩的啊,我说:好呀。
我们一次买了五十个币,因为买五十个送十个,这就是无可救药的消费者心理。我们逛了一大圈,最后在一台最无聊的娃娃机前停下来,我想要里面那只天蓝色的哆啦A梦。我太想得到那只毛绒绒的蓝胖子了,虽然不知道拿了它有什么用。男朋友对毛绒玩具过敏,那么可爱的东西他居然会过敏,他把家里所有带毛的玩偶都丢掉了,谈恋爱的时候也没有送过我。现在好了,他终于要和我分手了。可能早在半年前我们就该结束的,但一直拖到刚才吃饭他才说出来。他说他妈不喜欢我,他都三十岁的人了还要听他妈的话。他妈说我看起来像个坏女人,不适合娶回家,真是个非常棒的理由呢。
丢了三块游戏币进去,机器开始倒计时,扭动把手,抓,没抓着。再试一次,还是没抓着。第三次尝试,抓到了,但是又掉了。失败似乎更加强烈了我想要得到机器猫的心愿,尽管我真的不知道拿了它能有什么用。
我和徐烨其实也算不上老同学的,是啊,我们连同学都不算。我们既不是一个班的,也不是一个系的,甚至不是同一所学校的。我认识他是因为刘宁过生日那天把脚崴了,没有办法下楼去拿他送来的生日礼物,就是那瓶我也很喜欢的香奈儿。他还给她准备了一大包零食,里面的玫瑰牛轧糖真好吃,他大概不知道刘宁不爱吃甜食吧。他到现在仍蒙在鼓里,还不知道自己每次送来的吃的,其实都进了我的胃。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,那些东西都是刘宁不要了的,我吃的全是别人看不上的东西。所以越是好吃,我的心里就越是难过。
有一次平安夜,刘宁说:你呀别老是一个人在宿舍里面过,和我们一起出去玩吧。
这句善意的邀请真是深深地伤害了我,就好像我可怜到需要她施舍一样,在她的潜意识里可能我就是个孤僻又没有异性缘的家伙。估计我死了,也比她强不到哪儿去,我妈能给我带束花就不错了。
徐烨朝着娃娃机踢了一脚,他说:操。
这种机器很容易让人陷入赌博的心理,现在它不再只是我一个人的哆啦A梦,它成了我们俩共同的哆啦A梦。我们必须把被吞掉的钱找补回来,于是我去柜台前又买了五十块钱的币,再次赠送了我们十个。瞧,我们明知道这是个局,还偏要上套。
他说:他是故意这么设计的,骗子商家。根本就抓不住嘛,一只也抓不住。
别急,要保证好心态,刚才我看见有个男孩给女朋友抓到两只呢。我说。
两个快要三十岁的人杵在一台娃娃机前谈论心态,真是可笑。当时我就不该说那句好呀,我们应该分道扬镳,各回各家。
平安夜那天我记得自己也是说了一句好呀,然后就跟着刘宁他们出去了。过程就不说了,那天晚上刘宁与另一个男孩喝得烂醉,我和徐烨聊到半宿,后来不知怎么地就亲上了。我们几个全是单身,这么做本来也无可厚非,但我不清楚自个儿干嘛要撒谎。她问我们后来是不是全都醉倒了,我说是的。而他,似乎也没有告诉她真相。
回学校的路上,刘宁告诉我,她好像有些喜欢徐烨了。
我尽可能使自己看起来自然,我问:为什么突然改变心意了?
她说不是突然,他们俩从高中起就认识,日子久了可能就有感觉了吧。何况这些人里面,只有徐烨对她是真好。
哦。我说。
很多人不喜欢我说哦,他们觉得这样让人扫兴,那我更喜欢讲了。后来我们三个总是一起吃喝一起玩,这使我们看起来就像是真正的好朋友一样。说实话,有一段时间我也以为就是这样了,甚至开始有些享受这种感觉。
不玩了,徐烨说,找个地方抽根烟。
抽呗。我说。
外面的雨停了,我们围着垃圾桶抽烟,像某种仪式。
你说,她在下面会不会觉得很闷?我发神经了问出这种话。
嗯?
她如果还在,说不定可以抓到一只哆啦A梦呢。我说。
也许吧。
你还爱她吗?
不了吧。
那你爱过我吗?我说。
他迟迟没有回答我。虽然没镜子,但我脸上此刻应该有笑容,我也不知道那是狡黠的还是自嘲的,反正看不见。
树是什么时候绿了的?他突然像个哲学家一样抬起头盯住那棵树。
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?不知道,也许是两天前,也可能是七天前。我很用力地吸了最后一口烟,没吐,说完才顺着呼吸飘出来。
那天天是很蓝的,太阳很好,和今天下午的差不太多。徐烨把他姐的车开出来,仨人去龙源水库野炊。我还带了渔具,尽管我知道三个半吊子八成也钓不到鱼,钓上来的也未必能吃,但还是装模作样地带来了,毕竟不一定非要真的钓到什么。
那条浑浊的河来自水库的水,这里的泥沙量很大。我站在河边喝青岛,为了开啤酒瓶差一点把一根手指头丢掉,血往外冒的时候他们都吓坏了,我居然笑起来说:果然是瑞士好军刀。后来简单包扎了下就仿佛没事了,趁他们在搭炭火架,我一个人站在类似老家的那条河边喝青岛。
青天红日,烟尘滚滚,火还是没有完全点着。我和刘宁沿着河边寻找树枝木棍之类,还有一些废纸垃圾,也算是为环境做贡献了。但是火依然保持个性,不肯点着,更因为烧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烟雾变得浓黑而刺鼻。徐烨说车里还剩下些报纸,顺便把刚才忘了的果汁和蔬菜带下来,我说我和你上去拿吧。
后来我们大概去了很久,好像十五分钟左右,又好像是半个小时,还是快要一个小时。那些果汁蔬菜报纸可真够我们拿的了,但我发誓最初并没有打算拿这么久的,绝对只是单纯的好心和善意。太阳太大了,徐烨他姐的车里可真热,我都快要窒息了。我们做了一次,不对,应该是两次。年轻真好,如果放在现在我可能就体力不支了,毕竟环境比较恶劣。我在想,自己到底是在报复刘宁呢,还是存在其他种可能。
我看着他的眼睛接吻,后来就听到有人在拼命地喊救命。我们同时有了不好的预感,披上衣裳就往下赶,果汁和蔬菜也没有顾得上拿,我的手里却紧紧攥着一团过期的破报纸。河水看起来不是很深呀,怎么会没过她呢,她又是怎么掉下去的,该不会是故意的吧,她好像越陷越深了。我们没人会游泳,徐烨要跳下去救她被我拦住了,我说:你找死啊。
然后我就跑,想找个会游泳的人来救她。那些钓鱼的老头看着很近,可是我跑了好久才到,我气喘吁吁地说:有人溺水了,请你们救救她吧,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我们救了她,但她还是死了。她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死,真的不会是故意的吧,那她赢了。她连死了都是赢家,真是个厉害的女人,以至于我在余生都不敢提起她的名字。也许舅舅说得对,我可能真的是个不讲情义的人。
我说:我手里还剩下最后三个币,再回去试一次吧。
他可能想要否定我的建议,但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突然转变了心意,他说:好。
那只哆啦A梦依然安静地待在里面,但我放弃它了,干嘛一定要一只机器猫呢。扑隆,扑隆,扑隆,三枚硬币启动了机器。在倒计时里,我控制爪子,对准了新的目标。抓,升起,移动到出口。中途机器试图想要松开它,但被它紧紧地抱住,它成功地落进了出口的位置,真是好样的。徐烨伸出手把它取出来,送给了我。
心里仿佛尘埃落定,游戏结束了,有代价,可至少我还不是一无所获。我抱着这只来之不易的米老鼠蹲下来,开始哭泣。
以为他会问我为何哭,或者告诉我不要再哭了。而他只是在我身边,以同样的姿势蹲下来,摸摸我的头说:结束了,一切都已经过去了,不是你的错。
我听见我们同时长长地喘出了一口气,今天是清明啊。